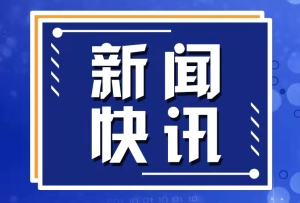若爾蓋濕地:歸來與重生
| 2021-07-07 來源:四川在線 作者:王代強 | 分享: |
哐當哐當……遼闊的大草原上,微風輕拂。平壩中,紅磚壘砌的小平房里,傳出一陣鍋碗瓢盆聲。

2號小型攔水壩施工前。(若爾蓋縣林草局供圖)
“快點搬咯!”7月6日中午,匆匆扒了兩口米飯,旦珍澤讓和父母一起,忙著將屋里的生活用品,往停放在院壩的五菱宏光小車尾箱里運。
天氣越來越熱,他們這兩天要把100多只牦牛和綿羊趕上山,并在山上扎起帳篷,享受近兩個月的涼快放牧。他們世代居住的這個地方——阿壩州若爾蓋縣麥溪鄉俄藏村,祖祖輩輩依靠草原、濕地,放牧為生。
“過去那片山上沒有水和草。”指著目的地,旦珍澤讓的父親卓瑪澤郎感嘆,幾年前,曾因牧場濕地退化,父子倆不得不遠走他鄉,輾轉全國各地打工謀生。如今濕地修復歸來,家鄉放牧活動又忙起來,他倆就是幾天前才回來趕忙的。

若爾蓋濕地保護與恢復工程1號攔水壩周圍的草(四川在線記者 王代強攝)
小小家庭的變遷,濃縮并見證了整個若爾蓋大草原濕地的重生。
作為全國三大濕地之一的若爾蓋濕地,濕地面積55萬公余頃,涵蓋若爾蓋、紅原、阿壩縣大部分和松潘縣北部區域,是長江、黃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養地,是黃河流經四川的主要干流地區,是“中華水塔”的重要組成部分,蓄水總量近100億立方米,為黃河上游提供30%水量。
這里還蘊藏著70億立方米高原泥炭,為全國之最,在調節氣候、保持水土、減少溫室效應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若爾蓋濕地保護與恢復工程實施區域。(四川在線記者王代強攝)
曾經的若爾蓋,因為氣候變暖、鼠害、無序開發、過載放牧等因素,濕地大量退化。隨濕地而“退”的,還有當地牧民和生活在這里的野生動植物。
近年來,隨著綠色生態發展觀念的轉變和相關工程項目的落地實施,退化的濕地得到治理、修復,像卓瑪澤郎父子一樣的“歸來者”越來越多。
退:
濕地退化,村民背井離鄉謀生
穿藏袍、戴藏帽,今年剛剛20歲的旦珍澤讓,看起來比同齡人更成熟一些。吃糌粑、喝酥油茶長大的他,最熟悉不過的是遼闊草原和汪汪濕地。
“很小的時候,就聽村里的老輩子講過紅軍在若爾蓋過草地的故事。”他使勁地挽起褲腿,比劃著說,紅軍戰士踏進沼澤,腿陷到了膝蓋。大家手挽著手,艱難前行。

老鼠曾在若爾蓋濕地打的洞。(四川在線記者 王代強 攝)
這樣的場景,屢屢出現在那些反映紅軍長征的影視作品中。“我以前去實地看了,像電視里那么多水的沼澤,已經很難找到了。”卓瑪澤郎擺擺手,說“水滿濕地”那是幾十年前的情景,現在的電視劇多少有些夸張。

若爾蓋濕地保護與恢復工程實施區域建設了圍欄。(四川在線記者 王代強 攝)
指著墻角一把鋤頭,50多歲的卓瑪澤郎,講述了他小時候的見聞。
上世紀七十年代左右,當地為了謀生和發展,大規模開墾濕地放牧。這是因為,濕地水多、泥稀,牦牛、綿羊一進去腳就被陷住了。于是,拖拉機、鋤頭齊上陣,開辟道道溝渠,將濕地中的水放出來,以便牲畜進入吃草。
“那時候一心為了吃飽,所有人挖溝的積極性很高,我家鋤頭都挖斷了幾把。”卓瑪澤郎說。

若爾蓋濕地一角。(四川在線記者 王代強攝)
濕地變草地,加之當時草場未分到戶,村民們無序、過載放牧,加速了濕地退化。
“更重要的原因,是全球氣候變暖,地下水位下降。”省林草局濕地保護中心負責人顧海軍說,近年若爾蓋濕地蒸發量持續大于降水量,導致濕地涵水變淺,甚至土壤裸露,出現黑土灘。

2號小型攔水壩施工后。(若爾蓋縣林草局供圖)
若爾蓋縣林草局提供的一張照片顯示,俯瞰若爾蓋一處濕地,絕大部分區域已經變成污水的土地。灰色和黑色是整個畫面的主色調,只剩少量黃色和綠色的草地點綴其中。近處,有一條彎彎曲曲、形似蚯蚓的小河,河中水面遠低于河岸。
濕地退化,直接影響當地村民生存。俄藏村共有90余戶450余人,基本都靠放牧為生。
“放牧多的一家有200頭牛、500只羊,少的也有20多頭牛、七八十只羊。”卓瑪澤郎掰著指頭算賬:大牦牛算800斤,一頭能賣六七千元。大綿羊算80斤,一只能賣2000多元。
隨著時間推移,濕地退化帶來的影響逐漸放大。俄藏村黨支部書記抗州澤讓說,到2012年左右,全村11萬畝草場中1.5萬畝無法放牧,村民不得不去外面承包草場。按70元/畝的價格算,全村每年將多支出100多萬元草場承包費。
卓瑪澤郎家有1100多畝草場退化,為此每年損失3萬多元放牧收入。“別人家的草場濕地也在退化,你給錢也很難承包到草場。”2018年,帶著剛成年的旦珍澤讓,父子倆打點行李(僅僅是幾件衣服),外出打工求生。

5號小型攔水壩施工后。(若爾蓋縣林草局供圖)
卓瑪澤郎幾乎沒上過學,旦珍澤讓只讀了初中,語言不通、技能缺乏的父子倆輾轉全國各地,在工地上搬磚、擰螺絲、賣苦力,嘗盡苦頭,一月工資不過四五千元。
每當看到工友們舉杯歡慶佳節的情景,父子倆總是望著漆黑的夜空,暗暗抹淚。他想念家鄉的妻子,想念美麗的大草原,想念那些牛羊,想念那一碗酥油茶、青稞酒……
治:
一座水壩,恢復一地生態
卓瑪澤郎的愛人,是個賢惠的妻子和慈愛的母親。
卓瑪澤郎和旦珍澤讓在外打工的日子里,她獨自一人騎著馬,放養著一小群牦牛和綿羊。
夏天晝長夜短,她每天早上七八點就趕著羊群出門,傍晚天將黑時又趕回家。9月以后,若爾蓋逐漸迎來風雪,可以上午10點多以后再出門。
她還要給牛羊擠奶、修剪羊毛,牽著牛羊、帶著農副產品去集市上交易。空閑時候,她也做些針織活兒,等春節來臨時親手給父子倆穿上,那是一年中屋子里最熱鬧的時刻。

5號小型攔水壩施工中。(若爾蓋縣林草局供圖)
7月初的若爾蓋,也是個熱鬧的季節。此時,當地白天氣溫在十來度左右,正處旅游旺季。
從縣城出發,沿213國道向西北行進,穿越熱爾大草原、花湖生態旅游區。寬闊平坦的公路上,牧民們趕著牦牛、綿羊,悠然游蕩,飛鳥成群結隊從擋風玻璃前劃過。掛著全國各地牌照的私家車走走停停,拍照打卡。
公路兩旁,青草織就的綠色地毯不斷鋪展,望不到邊,不時還能見到一個個水凼、沼澤或湖泊,在陽光的照耀下,閃著光。

若爾蓋濕地保護與恢復工程1號攔水壩周圍的草。(四川在線記者 王代強攝)
濕地是水的載體,水是濕地靈魂。“濕地就像海綿,既涵養水源,又調節氣候。”顧海軍說。
四川地處長江、黃河上游,濕地總面積170余萬公頃,以若爾蓋濕地最大。黃河流經此地,豐水季節徑流量增加29%,枯水季節徑流量增加40%。

若爾蓋濕地一景。 (若爾蓋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供圖)
筑牢長江黃河上游生態屏障,修復治理退化濕地,是當代人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近年來,一個又一個濕地修復治理工程項目,在若爾蓋落地生根。
“有二十多公分高了。”食指、拇指比個“八”,蹲在麥溪鄉政府外一片濕地中,若爾蓋縣林草局生態修復股副股長劉海金,徒手測量俄藏村這片濕地中草的高度。

若爾蓋濕地一景。 (若爾蓋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供圖)
若爾蓋濕地保護與恢復工程,從2019開始在這里進場施工。措施之一,就是將之前開挖的排水渠填上,同時修建新的攔水壩蓄水。
去年7月通過驗收的這項工程,總投資8880萬元,累計填堵排水溝35公里,恢復濕地水位6處,恢復濕地區域植被6400公頃,設置圍欄78公里。
跨越齊膝蓋高的鐵絲圍欄,記者走進工程實施區域,只見周圍一片綠色海洋,披堿草、老芒麥、燕麥等長得又深又密,三五步之內可見一個個水凼。“過去這些地方都是裸露的黑土灘,下點雨水很快就干了。”附近村民說。
再往里走,見到一處長100多米的“T”形1號攔水壩,迅疾的水流不斷從壩上漫過,流向下游各處。
劉海金說,過去這里是自然河道,雨水下來后,水面不過兩三米寬,現在有幾十米寬,將冬季枯水期水面高度至少提升了10厘米。記者下水實測,水深超過1米。而兩公里外的4號攔水壩因為水漲得太高,無法走近觀看。
類似地,該項工程在麥溪鄉、紅星鎮修建微型攔水壩152座。

若爾蓋濕地一景。 (若爾蓋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供圖)
記者看到,1號攔水壩上覆蓋了近30公分的泥土和牛羊糞,播撒了草種,青草已經根深蒂固。該項工程還設置了3年管護期,今年4月進行了補種。
顧海軍說,濕地修復的思路,是工程措施(修攔水壩)和生物措施(種草)相結合,堅持以自然修復為主、人工撫育為輔。
近年來,若爾蓋采取治沙還濕、種草還濕、滅鼠還濕、填溝還濕、濕地生態效益補助試點、濕地生態資源管護等方式,保護濕地生態系統,僅若爾蓋濕地保護與恢復工程就累計修復濕地9.6萬畝。
歸:
隨濕地歸來的,不止牧民
扔下行囊,沖進帳篷,揭開水壺,“咕嚕咕嚕”一口氣喝下三碗酥油茶——旦珍澤讓仍清晰記得,他2019年初在外打工第一次回家時的情景。
不過,這一次回家,他不再狼吞虎咽。“現在草原濕地恢復了,放養的牛羊又多了。我們這次要在家待一段時間,忙過這一陣子才出去。”他說。抿著馬奶酒,卓瑪澤郎指了指鄰居,“那幾家人也是前幾天回來的。”
隨濕地歸來的,不止牧民。

若爾蓋濕地一景。 (若爾蓋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供圖)
這幾天,若爾蓋濕地自然保護區科研科科長索郎奪爾基,領著科研團隊,進入花湖跟蹤調查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黑頸鶴。作為高原濕地生態環境的指示性物種,近年來,飛抵若爾蓋濕地繁衍生息的黑頸鶴不斷增多,已達1000多只。
在它們頻繁活動的花湖,面積從2009年的200多公頃,擴大到現在的600多公頃。保護區外曾經干枯的湖泊沼澤,如今又有水了。

若爾蓋濕地,黑頸鶴對天齊鳴。(若爾蓋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供圖)
多年未見的大天鵝,再次出現在俄臧村這片修復后的濕地。就連之前從未記錄到的羚牛,最近也在若爾蓋現身。
濕地恢復,離不開長效的管護。查看是否有亂搭亂建、破壞濕地草場等行為,為科研人員帶路……7月4日,紅星鎮河它村濕地生態管護員阿澤,又忙了一天。
為凝聚力量,若爾蓋濕地自然保護區聘請當地干部群眾作為巡護員、濕地生態管護員,全覆蓋對濕地資源進行管護。
從2015年起,保護區利用相關項目資金,實施濕地生態效益補償。“就是根據不同的濕地退化情況,采取禁牧、限牧、草畜平衡等方式,分別給予相應生態效益補償,引導牧民科學有序保護濕地。”索郎奪爾基說。

牛羊在遼闊的若爾蓋大草原上生活。(四川在線記者王代強攝)
對當地人而言,濕地是得天獨厚的發展資源。
在若爾蓋縣林草局對面,有一家“利生”酒店。老板陳姐說,因為冬季天氣極寒,酒店每年只在4月至11月營業。即便如此,這些年,由于濕地恢復,游客越來越多,她親眼所見縣城酒店賓館數量增長到40多家。為提升競爭力,她去年投資300多萬元,將酒店重新裝修。
生態好了,游客多了,收入增加了。僅2016年至2019年,若爾蓋累計接待游客近800萬人次,累計實現旅游收入約60億元。

若爾蓋濕地一景。 (若爾蓋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供圖)
在深入宣傳、政策支持、科學引導下,若爾蓋的農牧民們開始發展旅游、運輸、建筑等多種產業。
綠色生態發展的觀念,已在當地深入人心。在麥溪鄉,卓瑪澤郎等人自發成立濕地保護協會,組織志愿者沿河道、濕地清理垃圾,宣傳濕地修復,動物保護和垃圾清理。

若爾蓋濕地的黑頸鶴。(若爾蓋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供圖)
若爾蓋濕地,工作人員正在開展科考工作。(若爾蓋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供圖)
“草原、濕地是我們的家園,也是我們的財產,保護濕地就是保護我們自己。”卓瑪澤郎認識清晰。
夢:
一座公園,孕育一片夢想
“我們這里將建一個若爾蓋國家公園,這是一件好事。”麥溪鄉黨委書記尼西甲反復解釋若爾蓋國家公園的概念。
卓瑪澤郎雖然沒完全聽懂,但他說對了一句話:“公園里就是有很多植物、動物,自然和諧。”
此時,在距離若爾蓋500多公里外的省林草局,若爾蓋國家公園創建工作專班,正在為若爾蓋國家公園創建工作忙碌。
若爾蓋濕地,工作人員正在開展科考工作。 (若爾蓋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供圖)
“更好保護濕地資源,是創建若爾蓋國家公園的一大初衷。”專班相關負責人說,若爾蓋濕地生態價值、文化價值都很高,但對標國家公園建立標準,目前若爾蓋濕地在管理體系、治理能力和政策保障上還有弱項。
比如:管理上,由于多部門、分散化管理,未形成全面保護、系統保護的體制機制;治理上,仍以點線狀修復為主,缺乏“山水林湖草”綜合的、系統的治理規劃;政策上,生態保護資金以中省財政補助為主,多元化的保障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
若爾蓋濕地一景。 (若爾蓋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供圖)
在專班成員看來,創建若爾蓋國家公園,有助于理順現有的保護和管理體系,將重要的濕地-草原復合生態系統和高寒泥炭沼澤完整地、原真地保護好,以滿足黑頸鶴等珍稀瀕危物種種群不斷壯大的需求;既保證黃河上游水源涵養,又促進高原牧區生態保護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
“目前,我們的科研工作,主要是配合外面的科研院所來做。”索郎奪爾基分析了當前若爾蓋濕地生態資源保護與合理利用之間的矛盾:保護區內不少原住民還在以傳統方式放牧,缺乏長效生態補償機制,部分牧民減畜的積極性還不夠高。
若爾蓋濕地,工作人員正在開展科考工作。(若爾蓋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供圖)
在他看來,創建若爾蓋國家公園,將加大對若爾蓋濕地的保護力度,進而加大對當地科研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助于引入更多人才、項目、資金。
若爾蓋國家公園將由川甘攜手共建,堅持“大手筆、高起點、高標準”。此前,相關單位已完成對若爾蓋濕地土壤、植被、野生動植物資源等科學考察和研究論證,“申報三要件”已通過專家評審,形成了四川片區總體規劃初稿,正全力推進申報工作。
若爾蓋濕地,工作人員正在開展科考工作。(若爾蓋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供圖)
“我們將以創建若爾蓋國家公園為契機,打造全球高海拔濕地生態系統和生物棲息地和黃河上游水源涵養中心區,推進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新格局,打造‘最美高原沼澤濕地’新名片。”省林草局相關負責人說。
“在若爾蓋,除了能看國家公園里的美麗風景,還能品嘗到牧民家的地道美食。”這次回家,卓瑪澤郎謀生了創業夢。
若爾蓋濕地的黑頸鶴。(若爾蓋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供圖)
“濕地恢復得好,游客越來越多,打算在345國道邊上開間民宿。”說這話時,他底氣十足。